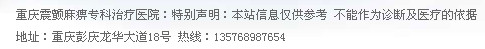在照片里重走故乡共七篇我的老家故
在照片里重走故乡
祝宝玉(安徽阜阳)
“还是用那双他们熟悉的眼睛看吧/慢慢看、深深记,把它们装订成册/放进心底,隔三差五拿出来/每看一次,我就重走了一回故乡。”读诗人秦时月的诗句,让我不觉念想起自己的故乡。
而今我的故乡在哪呢?恐怕也只能到照片里觅寻了。
五年前,我的故乡连同附近十多公里范围内的地下被探测出有丰厚的煤层,不多久,就有煤炭企业进驻,开始测量房屋、土地面积,之后是赔偿,拆迁,乡亲们被重新安置到另一个地方。从前年起,故乡所在的地方不断地下沉,先是村东头的田地开始坍塌,后来是村内的房屋依次倒塌。今年的中秋节,回乡探亲的我站在水岸上遥望“故乡”,那个不再存在的地方已经彻底从“地图”上消失了。翻看手机中存留的当年故乡的照片,不禁感慨,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永生再见不到了。
水井不在了,它的模样只能从照片中依稀辨识。井水永远是清澈纯洁的。清晨,乡亲们争相从水井里盛起太阳,装在桶里,挑着两盏红彤彤的太阳回家。我人小,力气也小,只能挑两半桶水,但也挑着两个红彤彤的太阳回家。每天,当鸟儿吱吱喳喳呼朋唤友结伴回家的时候,老牛伴着短笛踩着夕阳归家的时候,天上一片片红红黄黄的云霞,井里也出现一片片红红黄黄的云霞。
村头的树林曾是我们游戏的天堂,而如今,笑声只能臆想,画面要靠记忆描摹。小树林消逝了,对我来说,就没了四季的辩证,我体会不到春天的盎绿,听不到夏日的蝉鸣,尝不到秋日的瓜熟蒂落,踩不出冬雪的深浅足迹。我再不能漫步其间,没有枯黄的或暗红的落叶在微风中旋转的,踏不出落叶的沙沙响,体验不到身心的轻快,美妙声音突然消失,像音乐戛然而止。
故乡春天百花盛开的样子在薄薄的照片上,故乡夏日沁入心脾的河风在薄薄的照片上,故乡秋天金色抒情的诗句中薄薄的照片上,故乡冬日皑雪千里的姿态在薄薄的照片上……“议事大厅”的村头不再人声鼎沸,“泾渭之分”的篱笆黯然沉落,动人心魄的花前月下不复存在……乡亲们随意挥洒的眼神,还有村子里每个角落弥漫的泥土的气息,都成了思想深处沉淀的积忆。
翻看着那一帧帧虚拟的照片,我这才突然意识到故乡真的消逝了,而这刀割剑刺般的伤害所带来的疼痛才刚刚开始蔓延。
一次次回来,其实并没有走远,我只是在照片上重走了一遍故乡而已。
小村映像
高同先(江苏省宿迁)
小村
小村十分寂静,杨柳轻垂,斜阳掩映,几枝孤竹,几棵苍松,清旷疏朗,不闻鸡鸣狗吠。空落落的房子大多上了锁,锈迹斑斑。有屋开始倾斜,再来几场雨怕要成了墟地。那条通往村上的石路,爬满了绿嫩的草,踏上去,就像落在了松轻的毯子上,竟轻得没有了声响。
见到的第一人,便是一个佝偻着身躯,倚在窗前作遐想状,脸上满是沟壑的老汉。问为何这般岑静。老汉滑动着粗大的喉结说,早年还有千把人,如今,除了不管用的,都进城打工去了。他是个很热情的人,蹒跚地领着我们满村走。一路上,没碰到几个人。
若是碰到那些不上锁的灰墙宅院,老汉总要“咿呀”一声推开门,让大家看个明白,说了这是某人老屋及某人的故事,谁谁在哪儿打工发了财,一家子都进城了,好几年都未回来过;谁谁在外办了工厂,把父母领了去;谁谁嫁了城里人,买了房子……
黄昏余辉斜斜地照着小村,高柳蝉鸣,湖山横翠,秋风菱歌,晚云如髻。小村,一部内容时尚的线装书。
旧巷
一条美丽寂静的小巷。
假如是雨季,独自撑着一把油纸伞,对面再走来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戴望舒《雨巷》中的那种意境氛围即刻显现。或者看仕女长裙飘飘,虚空而云淡风轻,独步旧巷,客串所有唐诗宋词,情景定会令楼上望穿秋水的人儿柴扉不掩、房门虚设,只等那似人似仙的仕女千年仅有的回眸一笑。
旧巷不是很长,却狭窄,用条石铺就,两旁是门台院落,绿荫满庭,蔷薇盛开,莺啼蝶飞,轻风阵阵,隐匿在浓叶树枝间,看不清里头深浅。旧巷的墙斑驳沧桑,凝重厚实。
坐在旧巷台阶上,端一杯清香浓茶,慢慢品茗,品茗旧巷落寞凄凉,品茗人生荣华富贵、生老病死,很容易就能品茗出许多味道来。
旧巷,如细雨濯轻尘,洗尽了人生的烦恼和浮躁。
老屋
沿着土坡下来,黑黢黢的老屋出现了。
踩着满地的枯叶,小心翼翼地推开那扇沉重的木门。踅入老屋,觉得里头有一种陈腐的气味弥散,老屋冥晦和幽深,翠扇恩疏,红衣香褪,心里开始了悸动,仿佛一脚踏进了聊斋。
流光似水,物换景移,老屋主人早已进城了,扔下这幢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老屋,正屋三间,左右带走廊,花墙镂空,柱础石雕,都是慢工细活,讲究的东西,像一件件古老的艺术品。
庭院寂寞,粉蝶穿梭,蓼屿荻洲,茅舍竹篱,映衬着老屋,成印象派的画,美丽、缥缈而模糊。
小桥
村前有条小河,蜿蜒曲折,低徊缠绵。小河上有座小桥,由两块水泥板铺就,朴素自然,明丽清新。两头的桥墩长年立在水中,早已青苔密布,水草裹围。
小桥没有诸如双龙戏珠、凤穿荷花出水、龙凤呈祥等等传统吉祥的雕饰,也不曾读过甚至听过这桥有显赫的名声或者动人的传说,它只是一座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桥。也许是百姓捐资而建,也许是富人家行善积德之举,也许是谁家盖房余下两块水泥板而随手搭上。小桥终年累月静谧安恬,没有喧嚣,没有忙碌。有几个村人拉着板车、扛着农用工具一晃一晃地从桥上经过,也有几个散淡地歇息在桥上。
站在桥上就能看到很远很远一片金黄色的稻田,能看到斜阳、老树、人家,能听到阵阵的鸡鸣和鸟叫,还有桥下缓缓流过的水声。小桥宁静致远,如古旧画页,不生黯然苍凉,倒有一种难寻的温馨柔美。
渡船
小桥下游一里之余,水深河宽。河北是路,河南是田。田里有绿油油的菜园,还有满眼在飞的晴蜓、蝴蝶,张嘴一吸,全是湿润清新的空气。
河边泊一只菱角般的小木船,漆着褚红色的油漆,青苔浅生,歇在遮天蔽日的老树下。这船是用来摆渡的,一次能载十多人,大家叫这船为渡船,上街赶集,放学回家,好多人都要由这船载着过河,自行车、小毛驴、几袋粮食等物均可放在船上从这边运到那边。走小桥要绕好多路,没有渡船来得近便。
河堤上杨柳依依,芳草萋萋。对岸有水稻田、黄豆地、玉米林,还有工厂,那是一家个体木材加工企业,经常有车辆出出进进。从厂里回家,或从家里到厂里上班,大多数由这船载过河,还有拎菜蓝子的、挑担的、牵猪的……船的一头,盘着一团鸡蛋粗的麻绳,两端系在河两岸的水泥桩上。于是就有人争着去拉。这绳轻轻地一拉,船便在碧绿的水面上飘动了起来,平稳地走到河中央,走到河的对岸。
坐过一回渡船便久忘不掉,回想起来,有关渡船的情景依旧很美,仿佛是一幅静静的油画。
河埠
小河边,不知什么时候搭成了一个简易的河埠,两旁长满了花草,接着是沙石路面,卵石镶其中,从河边一直延伸到村头,仿佛河水与村庄之间的走廊,纤细乖巧,古朴典雅。
洗衣服、洗菜、挑水的村民们时常在这河埠上投下时长时短的身影。绿水盈盈的河道里,间或有小船驶来,载有几条水灵灵的鲜鱼,或半盆活蹦乱跳的青虾,或一堆黑乎乎的泥鳅,总会从石板砌就的埠头拎上岸。于是,河埠就有了躁动。水湿的卵石路上,踩着是一溜黝黑的大脚,滋滋作响,大人小孩,红男绿女,好奇地迎上前来,人头影影绰绰,越晃越多。
过了片刻,河埠就静寂了下来。半躺在竹椅上慵懒而松懈的老人,十分惬意地翕着眼,偶尔撑开眼皮望一下河埠,仿佛那儿有他年轻时的传奇经历;河埠一旁的垂柳下,正有一对青年男女相偎。河岸上杨柳依依,绿树成荫,河道里碧波荡漾,水草婆娑。这份河埠上的日子,悠闲自然,缓慢隽永,故事也就像清澈的河水不停地流淌着,愈流愈远……
舅婆的家常味道
王选(甘肃天水)
小时候,常惦记着去舅婆家,因为舅婆做好吃的。现在也是。几十年过去了,舅婆手指下的家常味道,像一枚枚指纹,永久的烙在大脑里,任时光如何磨损,都不会凋残。
秋天、冬天,去舅婆家,那时候新洋芋刨回家,大的,装进窖里,小的,用机器粉了洋芋面(淀粉)。洋芋面,铺在院子的塑料单子上,被秋天绵软的阳光一天天晒干,雪白,白的晃眼,用手抓,柔滑、细腻。天气不好,就得在炕上烘,三天,五天,慢慢干了。用细竹箩一遍遍箩,把疙瘩分出来,用盐水瓶子擀碎,再箩,再擀,直到洋芋面全部成了粉末,没有一粒疙瘩。最后,装包,架起来。
新洋芋面,做手擀粉,好吃极了。舅婆做粉,我有时帮着往灶膛里添柴,有时满厨房瞎溜达。
凉一碗开水,到温吞即可。把白矾提前碾碎成末。挖两碗洋芋面,把白矾末均匀的拌进去,再用水和面,一遍遍揉,揉成百下。和洋芋面,比和小麦面,难多了。和不好,擀不开。即便擀开,都成了碎片。有时擀成整块,一刀下去,全断了,半截,半截。洋芋面黏度低,柔韧性差,能擀出一手好粉条,在农村女人里,不多。这些完全凭借的是一份耐心,是一种感觉,是记忆深处的揉捏和把持。舅婆总能擀出又长又匀的好粉条。
柴火烧的水,在锅里翻成白花。下粉条。加两把火。很快,粉条熟了,捞碗里。千万不可过凉水。一碗热腾腾的粉条,撒盐,滴数滴酱油,倒醋,辣椒和花椒必不可少,且量要多。辣椒最好是自己种的,浇了熟油,红汪汪。辣椒和花椒,是一碗粉条的灵魂,它们完全决定着你是否吃的爽快,吃的过瘾,吃的仰天长叹。当然,撒点葱末,也好。最后,少不了的是熟油。胡麻油最好,菜籽油次点。浇了油的粉条,就可以下筷了。
一碗麻辣粉条,足以让整个萧瑟的秋末或者初冬,热意盎然,满心舒坦。此刻,故乡,不是一个人住了多久,而是有一种乡味,在舌尖麻着、辣着、过瘾着,永不弥散。
我们盘腿坐炕上,端着碗,吸溜着粉条,鼻尖上冒着汗。舅婆在地上,两手沾着洋芋面,笑着说,慢点吃,还有呢,看你们咋香来。
油煎果果,也是舅婆做的最好的。
提前一天和好面。面有白面、黑面两种,分开和。然后发酵。面起了,就能煎果果了。和面时,加盐,就是咸果果,加糖,就是甜果果。干木柴,朽掉的树根,舅爷前一天就劈好了,堆在廊檐下。要大锅,倒胡麻油。点火,锅热,油从锅底往上蹿细碎的气泡。干柴,很快就燃起了。汹涌的火舌,舔舐着漆黑的锅底。油热了。舅婆在一旁的案板上,把白面和黑面分别擀成饼状。一重叠,黑白面合二为一,卷起来,成棒状,横着切,像切萝卜片。然后把这些一层白、一层黑的面饼自由发挥,做成各种图案,这是个心灵手巧的活。蝴蝶、蝉、飞鸟、游鱼,各种各样。舅婆还会做花,最复杂的牡丹。母亲手笨,就做不好这么多花样,舅婆说,你干啥都大而化之,不细心。母亲笑道,都怪你,生的笨。
油开始冒烟。油熟了。放果果,轻手轻脚,一是怕溅出油,烫伤人,二是怕手重,捏坏了形状。果果进油,沉下去,很快漂浮到油面上,颜色由白变淡黄,最后金黄。要不停翻动,这样每一个果果受热均匀,不会焦糊,颜色一致。一锅果果,各种花鸟鱼虫,像极了百花园。
果果煎好了,捞到盆里,不能心急,稍等,待凉透。刚出锅的果果有点软。果果凉透了,油也没有了,吃起来才脆、酥。一口咬下去,胡麻油的清香,果果的干脆,让口舌生津,似乎到了七八岁,在六月的蓝格盈盈的胡麻地里奔跑。
果果耐放,能吃好些天。
蒸面皮,很费事,但舅婆蒸的面皮真好吃。这正是应了樱桃好吃树难栽。农忙时,是没时间的,只有等下雨天。我们坐舅婆家炕上,听舅爷絮叨村子里的事,舅婆在厨房忙活着。
先要到村里借面皮锣,得要一副,两个。
首先洗面。洗面前,用凉水将面揉成团,放清水里反复搓洗,最后,蛋白质和淀粉就分离了。然后沉淀。将沉淀后的清水倒掉。淀粉里放碱面,调成面糊。在面皮锣上擦一层油,将面糊倒入锣中,要适可为止,不可多,多了太厚,少了嫌薄。摇动锣面,让面糊均匀的铺开在锣上面。然后入锅,盖严锅盖。用柴火,火要旺。待面皮由白变成油黄,发虚、发胀,即可出锅,待凉。换另一只锣入锅,如此循环。洗过面的块状物,是蛋白质,另外蒸,出锅后虚如海绵,充满细密的小孔。这便是面筋。
厨房里蒸汽升腾,罩在屋顶,在房檐的缝隙往外渗。舅婆一丝不苟的蒸着。我们忍不住,下来了炕,在案板跟前守着,唾沫子直咽。面皮稍凉,从锣里剥下来,卷成棒状,切成一节指头宽。装碗,最上面放切碎的面筋,然后调盐、醋、辣椒、蒜,一勺熟油,即可。醋要集上散装的,拿瓶灌来。辣椒要带油。蒜要成末。调毕料,就可大开吃戒了。
一碗凉爽利口,酸辣筋柔的面皮,入口,入肚,那个香,一辈子在舌尖上打下了烙印。只要烟雨蒙蒙的日子,就想起柴火,想起升腾的蒸汽,想起迷人的面皮,想起舅婆斑白的鬓角,想起时光在屋檐上,滴答滴答的落着。
杏茶,偶尔在城里的早点摊上喝。白乎乎,跟牛奶一样,撒一撮杏仁末。喝起来,只有个淡到无味的杏味,完全没有那种带着微微苦涩的清香。啥东西,一进城,就很糟糕了。
舅婆能做很好喝的杏茶。
六月天,割麦子时,杏就黄了。麦割倒,能闲几天。山里杏子,无人采摘,熟透了,风一吹,嘭,掉地上一颗。嘭,又一颗。嘭,嘭……舅婆提上竹篮,捡杏子。刚落的,大的,好吃的,没有摔伤的,直接捡进篮。不好的,褪掉杏皮,留下杏核。半个下午,就能捡一篮子。
捡来的杏子,捏掉皮,串一串,挂墙上,风干。秋天吃,是很好的杏干,又柔又酸。在秋天吃杏干,总让人想起夏天大雨过后的森林里,有蘑菇,有青蛇,有穿蓝衣衫的外婆,在碧草深处走过。
杏核,在台阶上晒干。手里没活时,坐廊檐下的木墩上,垫一块砖,用斧头背砸杏核。使斧头,要会控制力量,轻了,砸不开,重了,砸破核,连里面杏仁都砸成了渣,就捡不出来了。啪,一颗,拣出杏仁,碎核拨一边。啪,又一颗。一小会,杏仁就装了多半白瓷碗。碎核也堆了一座小山。
最后,把杏仁在热锅上炒干,不要放油,杏仁里含油。要把握好火候,千万不可焦。带杏仁皮微黄,起泡,发皱,就可以了。出锅后,在案板上,用盐水瓶碾碎,最后用擀面杖一遍遍擀,成细末,就好了。
烧杏茶。小半锅水,水滚,均匀的撒上面粉,要快速搅动,不然有面疙瘩。待水微糊,撒上杏仁,反复搅动,最后放盐,一锅杏茶就好了。
一碗杏茶下肚,浑身通透。进城时,舅婆知道我和媳妇爱喝杏茶,把家里剩余的半塑料袋杏仁全装给了我们。每次喝杏茶,总想起舅婆,坐在屋檐下,脸朝着墙,一下,一下,砸着杏核。杏核和斧背的撞击声,清脆,明亮。舅婆砸着,没有回头,青布衫的背影,和满头的白发,在夏末的午后,被阳光反复照亮。很多年以后,我依旧还会怀念那个安静的午后,没有风,没有鸡鸣,没有农事,万物都散发着淡淡的苦涩的杏仁味,那么悠长,那么随意。
当然,舅婆会做的远不止这些,甜醅、扁食、时令野菜、洋芋丸子,还有好多。
舅婆越来越老了,满脸皱纹,牙齿也掉了不少。新衣服,也舍不得穿。每天,总是忙出忙进。我总是怀念着舅婆手指下的味道,像一种病,在大雪欲落的冬天、在阴雨不歇的秋天、在万物生长的春天、在日光漫长的夏天,在四季的所有骨缝里,我都被那些记忆中的味道折磨。
舅婆越来越老了。她对儿孙的疼爱,历久弥新。她手指下演变出的味道,历久弥新。
老城老家
卢慧彬(贵州贵阳)
我的外婆家,在遵义老城。
老城风水好,依山傍水,街巷纵横,自古繁华。传说当年张三丰得道成仙,路过老城,用拂尘扫了一扫,所以老城夏天没蚊子。我小时候每年暑假寒假都要去老城住一段时间。夏天好像的确没挂过蚊帐。我当建筑师的大姨爹对此的解释是,老城地下水丰富,地表温度较低,所以夏天较凉快,蚊子少。老辈人说,从前的老城,户户有院,院院有井。
遵义会议会址旁的子尹路,曾叫红旗路。红旗路上的何家巷,在纪念馆斜对面。小巷子,青石板。巷子里一口小方井。小井正对着我外婆家老屋的窗。
每天清晨醒来,就能听见“哐哐”的声音,那是人们在用水桶打水了。当时各家已接入自来水,小井的水已不作饮用水。但还是常有人来挑水。傍晚水被挑得快见底,第二天一清早,又是满满的一井水。水很清澈,冬暖夏凉。井上有青石扳搭成的方顶,避档天雨。井内壁用青石块砌得方整,年深月久,石块的棱角已磨圆,石缝长出水草。夏天,我在井前给五岁的妹妹洗头,我也才上小学。边洗边哄她,用泡沫把她的头发塑成鸭嘴形,说把她变成小鸭子,闭好眼睛哦。再打上一小桶水,把她头发冲干净。这时,外婆就在屋门口,唤我们回家吃饭了。
外婆总是在买菜做饭,做一大家子的饭。我们是个大家庭,周末聚一次,至少也有十多人吃饭。外婆一辈子没工作,就忙着给一大家人做饭带孩子。几个表哥表姐、我和妹妹、表妹,小时候外婆都带过。做完饭,外婆自己吃不多,就坐在老式架子床床沿抽抽纸烟。唯一的娱乐就是傍晚出去串串门,摆摆龙门阵。
那年表哥表姐一帮十七八岁,说都成年了,专门让他们坐一桌。一盘外婆做的夹沙肉,一片片切成薄片的肥肉间夹一层洗沙,上火蒸出来肥肉晶莹剔透,入口即化,肥而不腻。刚端上桌便风卷残云,一扫而空。而我们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却是外婆做的饭团子和酱油拌饭。菜做好以前,怕小孩子饿,外婆就舀瓢刚熟的米饭,用毛巾包上抓成团给我们,奇了怪了,完全没什么调料,吃着却非常香。或以猪油酱油拌饭,也是有滋有味。
老屋是木构架房子,四壁为木板,用报纸和挂历糊上,瓦片顶,大雨天会有一两处漏雨,用盆接水。爸爸、姨爹们每年要爬上房顶一次,捡去烂瓦,铺上好瓦。堂屋两张太师椅,一张八仙桌,一个神龛,神龛上并没供什么。再有就是两间小卧房,厨房里一灶一水缸。地板是泥地,未铺水泥,走起来包包拱拱的。外公是布鞋匠,听妈妈讲,他们小时候,就靠外公一个人的工资生活,夏天没人买鞋,没收入,已工作的二舅就把外公接到他家去。这狭小破旧的老屋里,外公外婆是怎样度过艰难岁月,抚大这么多孩子的呢?而我,从小在这老房子里,睡过最踏实觉,做过最好的梦,并在新年清晨最美好的时刻醒来。
我记事以后,外公的八个子女都已成家搬了出去,老屋就剩外公外婆和孙辈的一两个小孩,再大一些,老屋就只剩两位老人。每次我和妹妹从贵阳回去,总见外公在堂屋用他的老式唱片机或小收音机,听川剧或新闻,脚边蹲着他养的猫。看我们进门,他笑一笑,说“狗儿来了”。“狗儿”是外公对小孩子的爱称。过了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哦,是贵阳的两姊妹回来了。外公那时已经快八十了,他孙儿再多也不嫌多,常带我们一群孩子去街上,请我们吃一角钱一个的大汤圆。
小时候,我们从不缺布鞋穿,那是外公亲手做的。冬天穿他做的老式的黑布棉鞋,有个布带扣,很暖和。可那时浅薄,心里还嫌样子老气。现在才知自己有多傻。
最后一次见到外公,他还是送了一双布鞋给我,虽然是买的,不是他亲手做的。
常听妈妈摆老龙门阵:外公从鞋铺的小徒弟,变成师傅,解放前成了鞋铺掌柜,拥有过双合铺面;外婆的娘家则是开大药房家的。他们见过红军到遵义,经过战乱,迎过解放,也曾遭水患毁过家园。历经沧桑,见得繁华,也守得住清贫患难。
多年后故园已无家。老屋拆了,小井也填了。旧址早已变作一个酸婆婆菜馆,我也只是偶尔光顾的食客罢了。
一城、一巷、一井、一瓦屋、一家人,常在梦里见。路,靠我自己走。
那是一九九八
徐周豪(四川雅安)
那是年,我三岁半,生理上刚刚可以形成记忆反射的年龄。对于江南人儿来说,98年是一个灾难的年份,如我家,处于长江中下游的宿松境内,家门前不出五十米便是抗洪的第一道堤坝--同马大堤,这堤坝几乎承载了我们这些人童年的所有,或喜或悲。而98年,洪涛肆虐、风折杨柳的夏,挖空现在的自己也很难怀念出什么喜悦了。
那年98,梅雨时节,记忆中没有父亲,该在上海某处工地拉着钢筋水泥罢,家里光景不好,上有爷爷奶奶需要赡养,还有着我们姐弟三个年幼的孩子,住的是瓦房,墙的外侧因为长年顺流雨水的缘由竟是布满青苔,屋内湿气很重,墙墙角角的全是霉白,木板隔出的楼层老鼠吱吱的叫,大概是饿坏了吧。
连天的大雨,家里所有的盆盆罐罐都在屋内各处摆着接雨水,满屋的滴答,莫名烦燥。我这样一个爱闹爱跑的孩子也是被这大雨倾盆折磨得没了一点力气,安静的出奇。某傍晚,家门口的一个叔叔撑着一把大黑骨伞,也不全是黑,伞上补了几块红色的布,骨架断了一根,在雨幕中拖着一双草鞋来到我们家口,也不进屋,就在门口喊我妈的名字,我妈从里屋出来,叔叔说,圩外的水长了,该防汛了,让我妈妈准备好木桩,镰刀,这些防汛用的东西。我妈应了一声,叔叔就匆忙离去......
接下来几天,放晴了,却总是见母亲操持着些什么,经常清早扛着一袋木桩就出了门,晚上我们都入睡了才有琐碎的开门声。同马大堤隔着距离搭起了一座座棚子,整晚都有人睡在那,一部分人是防汛工作人员,而另一部分是房子被淹了暂时只得落脚在防汛棚。听大人说长江的水已经涨至堤坝,再涨估计会漫过来或者破坝。彼时我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看到大堤上整天都是人,很是新奇好玩,成天想着在那高高的土坝上玩耍。记忆中也是有这么一副画面,我们很多小人儿在那灰尘飞扬的土坝上奔跑,坝的一侧多了一排栅栏,栅栏下一两米处就是浑黄的江水,视线所及也尽是水,漫无边际,大人们抗着一包包沙子不断堆在水际线上。确实是新奇好玩啊。
故事铺垫至此,我发现我有些凌乱了,但我还是想继续说下去,后来,又下雨了,还是一场持久的大雨,更不好的消息是上游要开闸泄洪,那时没有三峡大坝,除了泄洪,上游人民也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困境。然后,全村的劳动力都集中了起来,晚上预计要在暴雨中通宵守护我们的生命之坝了,我妈也不例外,毕竟家里唯一的男人还在外拼着命,只有这妇道人家上了。
黄昏时分,雨歇了会,但天际还是混混沉沉的,估计在酝酿一场更大的风暴,母亲难得的在这洪涝灾害的年岁里给我姐弟三人弄了顿好吃的,有肉。我们年幼,自是吃的格外开心。母亲还是就着腌制的咸萝卜扒了几大口饭然后就戴起草帽在屋前屋后捯饬着什么,半饷,母亲拿着一个肥料的袋子,里面装的应该是几根木桩,母亲急匆匆的走到我们面前,一脸慈爱的看着我们欢乐的吃饭,但那份慈爱的眉目中好像藏着些许忧愁,母亲轻叹了一口气,跟大姐说,“敏儿(大姐当时刚6岁),你大些,晚上睡觉机灵点,妈晚上要守坝不能回来了,如果破坝了,大水来了,你带弟弟妹妹去楼上(当时瓦房,二楼都是木板隔出来的),水暂时淹不了那么高,你一定要护好弟弟妹妹,等别人来救你们”。说完母亲戴着那破旧的草帽就上了坝,消失在沉沉的天幕。
现在回想至此,我的眼前还是会泛起一层泪幕,也会感激起这上天来,幸之,那天雨就此停了,大坝没破,妈第二天一早拖着一身的疲惫平安归来。后来大了也常常从大人们茶前饭后的闲谈中了解那晚大坝差点就破了,正是有了千千万万的像我妈一样的母亲,惦记着家里的孩子,才玩命般透支体力守住了大坝。
老家是一坛陈年的美酒
孙庆丰(河北秦皇岛)
没有离开西部老家之前,我从不饮酒。到东部的一座沿海城市读大学后,我就慢慢地学会了饮酒。尤其是每逢老乡聚会,聊着聊着就聊起了老家,每每那种时候,乡愁就像四下突然钻来的冷风,每个人都会不自觉地裹紧衣服。
一杯酒下肚,从里到外身体就暖和起来,由嘴入心,甚至氤氲着方言的空气里,都是老家浓浓的味道。借着酒劲,我们就唱起童年时流行在老家一带的儿歌或者民歌,会唱的唱得忘乎所以,一颗未泯的童心,仿佛瞬间回到了老家,回到了纯真的孩提时代;不会唱的就跟着瞎哼哼,哼着哼着就有人哭了起来。然后就是你一杯我一杯拼命地饮酒,直到一颗颗心醉得一塌糊涂,乡愁的苦楚才算暂时得以慰藉。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们正处于为了人生奋发进取的青年时代,虽然我们在外思念老家,但却没一个大学毕业后想再回到老家,比起生活穷苦的老家,哪一颗年轻的心不向往繁华富裕的大城市,否则我们也不会十年寒窗即使拼上小命也要发誓走出老家。
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认为好男儿志在四方,所以对于“家”和“老家”的概念就一直处于混淆的理解状态。如今我们都天各一方,都已成家立业且人到中年,每逢在电话中或网上聊天,不知不觉就会把话题切入到“老家”。是啊,老家,纵然时光已飞逝了二十年,原来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无时不在念及着老家,念及着那片血脉相连的故土。
现在的老家在我们心中,已经不再是青年时所理解的,有一处能安身的居所就算是有了家。此家非彼家,即使我们身在天涯海角,那些浮萍般的家即使再宽敞明亮、富丽堂皇,也远不及让我们在无数个被泪水浸透枕巾的夜里,魂牵梦萦的老家。或许正因为如此,二十年来我们都还保持着饮酒的习惯,只是再也找不回年轻时一边饮酒一边唱歌,时而欢笑时而哭泣的那种氛围。
都说叶落思归,刚刚进入中年一颗颗心就迫不及待地想回去了。是啊,该是回去的时候了,二十年来,老家究竟变成了什么样,我们能为老家做些什么,随便找一个理由,即使没有理由,作为一个当年从老家走出的孩子,我们也该像一个心怀感恩的儿女一样,去看一看我们含辛茹苦的父母。
约好了时间,我们就从天南海北出发,老家是共同的目的地。生活有时真得很奇怪,年轻的时候一心想离开老家,现在我们却哭着喊着都想马上回到老家,甚至恨不得立刻能长出一双翅膀。
当我一踏上那片久违的故土,瞬间就被眼前的一幕幕惊呆了。着实说,对于老家最深刻的记忆,我还停留在二十年前那个穷苦的时代。那时的老家,没有楼房,没有汽车,似乎现在所拥有的,二十年前什么也没有。感谢这个光明而伟大的时代,城乡一体化的快速发展进程,使得现在的老家简直就成了传说中的世外桃源。
可以说它是田园中的城市,也可以说它是城市中的田园,那种独具老家韵味,宛若一坛陈年美酒的老家风情,使得老家如今已享有了很高的知名度,成了镇里发展乡村旅游的示范品牌,据说,政府正努力将老家打造成国家级农业公园。
让我尤为感动的是,如今的老家已经建起了乡村文化活动室,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家书屋等重点文化惠民工程,以及乡村学校少年宫,留守儿童活动室,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等,使得乡亲们不仅在物质上,就连精神世界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盈。
走一走,看一看,转过身,把童年时的记忆再梳理一遍,旧时的穷苦与破败早已荡然无存,每走一步,都禁不住让我泪流满面。本来我们约好了,要一起找寻童年的记忆,可走着走着就走散了。是啊,或许是我们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记忆,亦或是我们不再是童年时代那群一起玩耍的小孩子,也不再是二十年前同在一座城市读大学时,为了排遣乡愁和寂寞,而经常聚在一起饮酒的热血青年。
夜晚的老家,比起白昼让我更感觉温馨醉人,因为走着走着我们居然都不由地又聚在一起了。那座给了我们知识和鼓舞的乡村小学,仿佛童年时的读书声仍不绝于耳。这算是宿命,还是我们注定会拥有的人生,从原点出发,绕了一大圈,最后又都齐刷刷地回到了原点。
但再次回来,我们的心中却充盈着无限的幸福,还有,就是那么一丝惭愧,二十年来,我们没有给老家做过什么,可老家迎接我们的,却依旧是无私而温暖的怀抱。就像在白天,那些善良的乡亲们一个个和我们热情地打招呼、握手,有些老人还唤着我们的乳名,仿佛我们还是那群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再次相聚,免不了要一起饮酒,虽然大家都带了全国各地盛产的名酒,可在老家的土地上,我们却再也品不出任何滋味。有人提议,我们饮水,饮老家的水,饮着老家的水,却饮出了美酒的香醇和馥郁。是啊,二十年来,老家何尝不像一坛陈年的美酒,一直在我们的心中封存着。美酒开启的那一刻,我们又唱起了歌还跳起了舞,我们都醉了,但却从来没有醉得如此幸福!
扬州仙女庙有一条捞米巷
张怀珊(江苏南京)
我的家乡在扬州仙女庙,镇上有条捞米巷,不是地地道道的老仙女庙人,恐怕知者不多。就像北京人爱提王府井、上海人爱提南京路一样,仙女庙人怎能不提老街——龙川街呢!上了老街为上街进城,离了老街算下乡,信不信由你,老街人就认这条理。
捞米巷位于龙川街中段、利民桥东五十米处,向东是糖坊巷。捞米巷不深,长不过三四十米,挂捞米巷门牌号的也就一十二户。
捞米巷因何成名?巷子里何处捞米?何人在捞米?真应了一句老话:说来话长。捞米巷头曾开过一爿张万源烧饼店,张万源是烧饼店的老字号,烧饼店的老板叫张玉书,倘若健在也该有一百三十多岁了。张老板生就一副慈眉善目,打烧饼炸油条手艺堪称一绝,烧饼皮子崩脆,底子不焦,瓤子绵软,口味极佳,油条黄亮亮、胖乎乎、劲抖抖,讲究入口不涩不腻不苦,带甜带咸带香,却从不放半点糖星盐星香精星,功夫就在手头筷子的“拨”上——“三分油炸七分拨功”。远近四乡八集上街的人就爱吃张万源店做的那一口。烧饼两文铜钱一个,油条一文铜钱一根,几十年不涨不降。童叟无欺,遇有手头不便的,饥肠难熬的,未付铜钱,张老板也不计较,更不会在粉板上记上“xx欠铜钱几文”一类的混账。故而张老板人缘极好,人缘好人气旺,人气旺生意就不错。
张老板膝下三女,招爱徒为上门入赘三女婿,改名张继生。张继生继承了张老板的衣钵,店里的大小事一应由他上下打点。张老板落得轻闲自在,一日忽发奇想,找铜匠打造了一柄特殊的大铜勺,铜勺一米多长,铜勺青花碗般大小。原来,张老板见河边口(利民桥与江都桥之间)每天淘米来的人大多有米粒撒落河边水中,加上该处乃米粮集散码头之一,落入河中粮食不在少数,于是他拿着大铜勺清晨和傍晚都在河边一铜勺一铜勺的从水中捞撒落的米,寒冬酷暑从不间断。张老板让老板娘和媳妇(其三女婚后不久即因病不治而故,老俩口开明达理,又作主替张继生续了一房媳妇,一家人和乐融融从没丝毫芥蒂,非常难得难能可贵矣)在院子里扎了篱笆,养了几十只鸡,鸡食就是这捞来的米。
张老板养鸡可是与烧饼油条大有关系,因为在面肥发酵时,一定要加进原汁原味的鸡汤,不过用什么鸡,加多少汤,什么时候加汤,那可是绝活,只有张家翁婿知道。
张老板扛铜勺捞米成了巷子里的一道风景线,老街人遂称小巷为“捞米巷”。
后来张老板将铜勺传给了二女儿,熟悉的人都爱称她为“二嬢嬢”,二嬢嬢女承父“好”,每天都爱左手拎一只小木桶,右手拿着大铜勺,到河边捞米,家中也养了一大群鸡,到老都一直酷爱养鸡。
张老板夫妇、张继生夫妇、二嬢嬢夫妇早已仙逝,捞米巷还在,前几年龙川街东半边改造成步行街,捞米巷也就成了老街人的记忆了。捞米巷不再捞米了,张万源烧饼店随着公私合营也改成老住宅了。捞米巷老住户仅八家。小巷里走出了总工程师、厂长、经理、校长、主任、教授、大夫,市政协委员还有两三位呢。
说来造化有趣,张老板家的门牌号是龙川街89号,后来一度“破旧立新”,换为过前进街3号。二嬢嬢家的门牌也上了解放路的号码,他们的居宅竟与捞米巷名无缘挂上边了。
龙川步行街改造建成亮相后,张家后人也和老街人一样搬离了捞米巷。捞米巷和糖坊巷、天聚巷、大坟滩巷、闽家巷、高坡台巷、一人巷等巷,连同那东边半条老街上的长长麻条石,都化为乌有了。就像江都仙女庙、禹王宫、都天庙、螺丝庵、过街楼、大南滩、小南滩、臭水汪、方家祠堂、三板桥、又山大和尚庙、小虹桥、菜市口、星街、佛照楼等古迹古建古处一样,空有其名,而无其实。不过,我的乡愁梦里依稀在,几度夕阳红哟。
-----------------------------------------------------------
附:
“我的老家故事”征文比赛启事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献礼国庆中科白癜风帮扶献礼国庆中科白癜风帮扶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dihd.com/zcmbhl/7766.html
- 上一篇文章: 时政要闻易引起性早熟的食物黑名单
- 下一篇文章: 演示清醒气管插管麻省总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