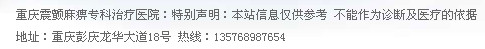于坚五千年的中国在最近三十年被完全的拆迁
作家简介:于坚,第三代诗歌代表性人物,强调口语写作的重要性。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今天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最大的现实,
文革在时间上拆迁了中国,把中国过去的历史变成了一个空白,过去的历史完全被妖魔化。我经常听到年轻一代的作家谈到中国历史的那种虚无感,把中国历史看成一个灾难、死亡、灰暗,一切不幸的根源。我们成了一种没有时间的民族,成了一个年轻的民族,我们置身在一个任何一种历史都没有经历过的一种全新的世界之中。
神话里面的尤利西斯离开他的家乡到大海上去流浪,也可以说他正在面临一种拆迁,但是流浪的终极是回到了他的家乡。虽然故乡人已经不认识他了,但是尤利西斯家的老狗认出了他,因为那个狗还记得他的气味。唐朝诗人贺知章离开故乡到各地去流浪,最后也回到他的故乡,虽然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但是他乡音无改。
而我们面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拆迁的结果是我们的故乡没有了,谁也没有故乡,你即便是从未离开你的故乡,你也在你的故乡变成了一个被流放者。所有的人离开他的故乡搬进新的社区,丧失了邻居,丧失了童年的老树,丧失了给你糖果的大伯,你完全成了这个世界的陌生人。你搬进你的社区,然后你噗通一声关上门,你和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关系。
人和世界不再发生关系,我们不再发生传统的文学创造的那种关系,《红楼梦》里面那种人的关系。我们完全进入了一个陌生人的社会,没有任何联系,每个人都住在一个铁笼子里面,整个世界都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国世界成了一个个碎片。
我认为这并没有在中国的文学里面被表达出来。我记得李鸿章在年前就说过,“中国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王国维他们也都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中国这样的先知他们只是意识到一种历史的即将发生,而我们正是亲历了何为三千年历史之巨大的变局。我们已经完全置身在和中国过去的历史断裂的那么一个时代当中。
我最悲伤的是我过去写滇池的诗现在都是一种谎言,因为这样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比如说我看今天《红河文学》还有很多乡村的风花雪月,这些东西都像谎言一样。文学变成了一种谎言,因为没有和它对应的经验和现实。30年前我来过蒙自,蒙自今天已经是一个焕然一新的新城,和上海郊区的某个城市有什么区别?你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你感受到的生活世界完全是一样,没有任何区别。
20年前我来到滇越铁路的车站拍纪录片。滇越铁路是从昆明一直到越南的,是法国工程师设计,由中国工人在年前建起来的一个铁路。这条铁路使云南绕开了中国高山大河的阻隔直接和这个世界联系起来。这条铁路它修建的时候云南还是一个蛮荒之地,那些古老的部落、古老的歌谣、一个自足的世界。忽然滇越铁路像外星人的飞船这样呼啸飞过蛮荒的高原,带来的一种完全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世界。
可以想象一个苗族村庄的刚刚出来要到自己家的土地里去收土豆的农民,怎样躲在丛林深处看见这个可怕的东西穿过他的土地。年前这个滇越铁路的火车就像今天的现代化一样,它是现代化早期的声音。
过了70年,当我去碧色车站的时候,这个车站已经被废弃,日本进口的、美国进口的、德国进口的旧的机车头,全部烂在碧色车站的车站。我小时候就坐过这个火车,曾经认为现代主义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走向未来的伟大的力量,每个人最终都要搭上这个火车。但是忽然看见这些火车变成了一些生锈的恐龙,躺在那个车站里头,我非常感伤。
这个车站使我思考时间的问题,时间到底是什么?难道人真的是不可一世,没有管制人的东西吗?后来我拍了一个纪录片,叫做《碧色车站》,然后这个纪录片曾经入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银狼奖。我发现我的电影在西方放映的时候引起知识分子的,也正因为这个电影我多次前往西方,在我少年时代的印象里面就是中国太落后了,中国需要一个发达的社会。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在70年代末有一天中央电视台出现一个台北街头的镜头,我们看见台北的大街上全是汽车,所有的人都尖叫起来,不可想象。然后我们认为新世界就必须是这样的,旧的中国应该抛弃。
我到了西方,到了很多国家,我发现他们并没有抛弃旧世界。我们现在就坐在我们30年前所梦想的天堂,但是我们是否感到非常的满足?今天我们终于发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在所谓的前面,所谓的未来。
我昨天去碧色车站看到挂着一个巨大的标题,“早日签订拆迁的协议,早日走向幸福。”年后这是一个村庄,是美丽的乡村,无数的石榴树已经长出来,农民用石块建造了自己的家,在家里边有鸡、有狗、有鸭,但是现在这些计划是要把这些全部搬走,然后建一些什么景观。
这是在进行一种同质化的拆迁,他们意识不到在建筑后面是生活世界。你把这些建筑拆掉了,你就拆掉了生活。本来你的邻居在这里30年都在卖着你非常喜欢的小吃,拆迁后你永远找不到了。本来这个旁边是有一棵老槐树,拆迁以后这里变了。这个是没法逆转的。最后所有的滇越铁路的车站都变成一个车站,一个仅仅以商业为目的的车站,生活世界完全消失。
云南的丽江就是一个例子,大约在30年前去的时候那是一个充满神奇的地方。在那里可以看到玉龙雪山,在那个城市最伟大的不是人,是山上的神灵。现在除了旅游的洪水和商业街什么都没有。每一个摊子都在卖伪装的工艺品,没有任何生活气息。
如果这个世界上不存在这些东西,你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丽江式的景观,那么不会有文学。我觉得同质化可能对平庸的大众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但是对于作家来讲就是灾难,因为最后文学将丧失细节。而在中国同质化的这个浪潮比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都严重和可怕的多。
因为同质化和西方文明有关系。我认为西方文明从希腊时代开始,一直到启蒙运动,它都在进行同质化,比如在希腊时代是一个众神狂欢的时代,那是一个有奥林匹克山,有宙斯、有狄安娜等等有各种各样的神的时代。柏拉图的理论、苏格拉底的理论就在那个时代诞生。就像中国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一样,有孔子、孟子、韩非子。但是后来伯拉图主义占了上风,他认为世界是有一个完美的理念的,根据这个理念我们可以创造一个理性的、模式的世界。后来基督教的兴起就是认为只有一个神,其他的神都是异教。在中世纪,中世纪就把异教徒,把那些在云南高原上还存在的部落中的巫师全部消灭掉,烧死,用一个教来统治世界。最后到了工业革命,上帝摇身一变成了市场、经济、商业、科学。
今天同质化实际上是在用科学技术、商业来统一这个世界。只有一种生活方式是值得过的,其他生活方式都是落后的、愚昧的。你要活的像样你就必须有大房子、汽车,就要吃面包、喝牛奶,这是一种方示。但是你还可以像桑丘和唐吉坷德两个人一样去流浪,那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像吉普寨人那样去流浪。但是同质化最可怕的就是认为只有一种方式。
在西方的文明里面,对这样的这种世界观的怀疑、批判和反抗一直是西方文学最伟大动力。无论是卡夫卡还是托尔斯泰,或者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契诃夫,他们的作品里面都有一个根本的主题,就是对于这种科学主义的商业主义的技术化的未来的怀疑。
卡夫卡他在世俗的人生里面是非常成功的,他是保险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干得很好。但是他所有的写作都指向对这种生活世界的怀疑和反抗。
20年前我是读不懂卡夫卡的,你的那个世界难道不是我们要追求的吗?有一个好的工作,有稳定的丰厚的工资,还痛苦什么?这是一种伟大的痛苦。就在于他后面的世界观,他的写作是基于人为什么要有这个世界?这使得他才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我这个人的生活习惯是先吃早餐然后去漱口,我吃完早餐回到房间的时候看到服务员正在整理我的房间,我的心情就很坏,因为这种旅馆的房间是最标准的同质化的房间,都一样。无论在巴黎、无论在上海、北京、昆明,放下两只牙刷、一块肥皂、白毛巾、脚垫,然后把你的枕头叠的四四方方的,你扔掉又拿过来叠好。我好不容易睡了两天把我的习惯带进这个房间,这个房间变成我一人的房间,我的味道、我的混乱进去,他又把我标准化了,把我气得要死。我就跟那个小姑娘说你不要给我搞这个事,你让我每天晚上在那个光滑无比的床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就是太难受了,我好不容易把这个床单磨合得适合于我的身体。那个小姑娘就说这是规定。我也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不要小看这么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是象征性的,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一个被一个模式规定的世界里面。只是说这种规定和纳粹德国的规定不一样,纳粹德国的规定是你必须去死亡,因为你是犹太人。那么这个规定是什么?如果你想做一个人,我就规定你只有这种生活方式才是人的方式,如果你要以别的方式生活,你就要被灭掉,这就是每天在各种细节上的规定。
大家有没有看过《清明上河图》,那是一个没有规定的混乱的世界,想怎么做怎么做,桥是弯的,摆摊人东一个西一个,但是今天这个社会城管认为是脏乱差,他要让所有的人去超级市场里买东西,他不知道那种超级市场就是过去的这种集市,对于我母亲那代人那是一个节日,那是使我的生命好玩,不会空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以前是有很多街市,一到赶集这一天就是每个人的节日,换上最好的衣服走在那个集市上,有来自各种各样的意想不到的土产出现在你的面前。比如说你会发现一只山鸡。现在的超级市场它除了付款购物之外和你没有任何关系,都是陌生人的市场。
同质化简单地讲就是细节的消失,而文学最重要的细胞是什么?就是细节。没有细节你怎么当小说家,你怎么当诗人。任何一篇小说都是细节造就的。你看无论是契诃夫的小说,无论是卡佛的小说,我最喜欢的小说都是从细节开始的。但是从细节开始的小说在中国我觉得是比较弱的,中国小说喜欢从宏大叙事开始,不会从一个牙刷的位置没有摆对,因此发现这个房间里面可能出现的某种故事这样的细节。门罗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其实很多年以前她还没有获奖之前我就读过她的小说,我读完之后我说这个人要获诺贝尔文学奖,那可能是发生在她获奖的五年以前。后来有一天忽然听见这个获奖的名字,然后又看见这个小说我是看过的。她的小说充满着细节。为什么中国当代的小说我觉得缺乏细节,这个不怪作家,我认为细节在一天一天的消失。
没有细节,每个城市都是一样的,每个房间都是一样的,连你做爱的床摆的位置都是一样的。但是在西方的作家里不一样,西方有那种任何一件事的发生都会有很多人在想为什么的传统,中国人不是一个思的民族,我们不喜欢思,只喜欢入世,你不会思考我们周围发生了什么。但是西方不一样,工业化在18世纪就开始,所有的作家、哲学家、诗人都在想我要不要这个东西?另外他有很多结论,比如说马里雅蒂他是未来主义的诗歌领袖,他就认为未来是最好的,我们要歌颂钢铁、歌颂工业、歌颂未来主义,未来主义是肯定未来的否定过去的。未来主义它起源于西欧,但是它生根结果的地方在哪里?在苏联。苏联就是一个未来主义的社会,彻底斩断俄罗斯的历史。
我不知道在座的作家有没有思考过,这种腐败到今天如此严重触目惊心的程度,后面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文化出了问题。在腐败的后面是一个文革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已经弥漫整个中国,新的就是好的。在新的就是好的这种文化的影响下我们拆掉了传统的中国,画栋雕梁,我们的中国是手工的中国,过去的中国是手做的,今天的中国是机器计算机,我们建立那么多的假大空的鬼城,所有的会议都变成了一种空洞的、要铺着红地毯的会议,现在文化开始箫条了。因为离开了这种麦克风、红地毯、什么歌星演唱这种文化,今天人不知道怎么搞文化。那种文化就中国过去20年的文化,如果在世界的文化史上完全是个笑柄。任何一个作家、艺术家、诗人的活动开头都是领导要说话,说和这个活动无关的话。百花文学奖要请我,本来我今天要在领奖的,为什么我没有去?我看见议程在那里有一个作家要走红地毯我不去。这完全是太愚昧的。但是我发现,我们已经完全没有意识,就是这种文化已经深入到骨髓,我们不知道正常的常识意义上的文化,有很多正常的事情我们都认为是一个奇迹。
今天中国当代写作非常危险的就是我觉得他越来越变成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就是今天是一个歌德所谓的世界文学的时代,歌德曾经希望这个时代,但是这个时代遥遥无期,那么今天科学技术的进步、互联网的发达,使我们被迫的置身于世界之中。我们再也不要以为你是在蒙自,你无法在世界之外写作。世界就是你门前的高速公路,这个高速公路和美国的高速公路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面对的经验是一样的东西,你都会面对高速公路的经验,你都会面对这个公路上刷新的车祸,你没法说你的写作依然只是民族的、地方的。这个可能是一个被迫的,完全被迫,但是你必须接受这个现实。
80年代中国忽然对世界打开门,各种各样的知识涌进来,我们经过文革的地下阅读,也经过80年代开放的阅读,我认为我的知识谱系是一个基本的世界性的知识谱系。《莎士比亚全集》那时候我是从头读到尾,我青年时代读这些书三天就要读完,我可以把这些书读完再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朋友听.
比如说我在西方和各种各样的诗人作家来往,谈到的话题,提到的知识都不会陌生。但是如果年轻的一代认为写作是指向未来的,过去时间这个东西是无所谓的,那么这实际上会使你的写作变成一种封闭的地方性知识,你就没法在世界的写作里面对话。
像莫言的小说那样的以一种传奇去取胜,就是中国的地方性传奇,这个时代可能是最后一次,未来的作家你要想再靠那样的传奇取胜是不可能的。过去这个世界上是有无边无际的部落,但是这个世界今天已经变成一个全球村,全球村并不意味着每个民族的图腾之间不再交流,依然在交流,这就是所谓的文化软实力。我有一年去日本,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日本诗人非常严肃地告诉说日本的年轻一代已经起来了,他们非常有信心。那种口气就像奥运会较量一样告诉我。
就在你玩地方性知识时,村上春树在玩的已经是世界联系了。几年前我的一个法国朋友告诉我现在法国的文学已经衰落了,没有中国的文学那么生动那么有活力,但是过了五年我再见到他,他又告诉我说现在我们法国出现了几个非常了不起的作家。最近我看见一个法国女作家的小说,叫做《地下时光》,写的真是好。我觉得法国60年代的作者完全是我青年时代所看见的契诃夫一代作家的延续。
我讲这两个故事的意思就是说虽然都是在一个同质化席卷全球的时代,但是作家并没有丧失想象力,生活也没有消失。上个世纪的先锋派文学深受西方小说的影响,尤其是受罗伯格里耶这些作家的影响,那么罗伯格里耶他的小说他主要是基于他对时间和现实的理解的角度的改变。那么他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实际上他是把时间拉长,把现实变小,把工业体系的测量体系用到了小说里面来,他的小说是测量的,你都可以看见你的房间有多长,是立体的还是方形,他写这个东西。有一段东西你琢磨这种东西发现中国的当代小说受这些东西的影响太大了,有时候我偶尔也会看,但是我觉得罗伯格里耶这样的作家他后面没有卡夫卡那样的悲悯之心,对世界的那种意识,没有那种历史意识和那种世界观,所以他那一代的作家,60年代的作家今天已经玩的是过时了,就是除了中国之外。当现代主义的浪潮过去之后,读者喜欢的还是那种能够使他们的灵魂,他们的人生获得意义的那种,他们重新去看巴尔扎克,去读莎士比亚。
上个月我和欧阳江河住在巴黎的左岸,晚上出去散步,超现实主义就是在附近的一所房子里诞生的,他们在这里开会,而我们住的那个旅馆是马尔克斯写一个《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这篇小说的那个旅馆,他就住在顶楼,一切都烟消云散。
古代中国有整一的世界观就是道法自然,无论是诗人、无论是画家他都是道法自然,自然在中国不仅仅只是一个教科书里边的自然概念。道法自然,就是自然是一个教堂,是启发我们如何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它是神灵、它是上帝,所以是道法自然。过去中国的文学艺术都是有这么一个基本的世界观。但是这个世界观被摧毁,今天我们受西方的影响,自然变成了一个可以开着推土机随便摧毁的地方。
西方文明的世界观是什么?是天堂不是大地。西方文明不信任大地,所以他发展出数学、逻辑、分析等等,就是认为大地通过科学是可以重建的。60年代人们认为喝牛奶身体就会好,甚至还可以长寿,就疯狂的喝牛奶,最近我看联合国的报告根本就没有什么证据证明。西方文学认为什么都是可知的,中国文化他讲阴阳,那么阳是有,阴是无,那么世界既有可知的部分也有不可知的部分,这两者的不断的运动,那么生命才会诞生。如果你只是讲阳,今天这个实际上就是只讲阳,只讲有的一面,完全不讲无的这一面,那么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实用,越来越乏味,虽然是如此辽阔的一个世界,但是只有一部电梯。
写作是对无的一种守护,作家、诗人是我们今天这个日异月新的时代最后的手艺人,他的写作都是来自人类的原初时代。为什么人类要有作家?要有诗人?这个问题不是未来告诉你的,是过去告诉你的。因为人意识到无的存在,意识到无的恐惧,无的地位,虽然现在已经认为我可以搞定一切,电梯有了,高速公路有了,每人一瓶矿泉水,但是你还是没有搞定。明天会不会地震你知道吗?一场地震就把你所有的你自以为牛逼烘烘的一切就打回最原始的荒野上去了。在那个时候,在原始的洪水袭来的荒野上地震的时候,和你在一起的只有神,只有无,什么都摧毁了,在那个时候你的内心需要战胜恐惧,这时候你需要的是诗。诗人是什么?诗人就是最早的巫师,当一个部落在洪水或者是闪电的恐惧之中忽然有个人站起来对着天空说了一些什么,毫无意义的话,那个人出来说了,语言开始了,于是我们大家安静下来了。这个人就成为巫师中的领袖,屈原就是这样的。
印度到今天很多仪式上依然要念七千年前流传下来的古歌,已经没有人知道这个歌是什么意义。但是他就是要唱这个歌,你知道有什么意义吗?那就是使你在你不可知的世界里,你的心能够觉醒、安静,你不再惧怕控制你的东西,这些远古的声音后来产生了文字被记录在甲骨上流传到今天。那么我们的作家就是继承这种远古的,所以你无论怎么写,你无论怎么玩弄形式,我觉得诗还是孔子说的都是兴观群厌。
“兴”是什么?心就是赞美。古代世界因为为什么兴在第一,因为古代世界的中国人他生活在中国这个地方,古代的中国是水土丰美,河流、高山、草原、森林、百兽,人对大地的关系是感激,中国最古老的诗歌第一首文献可以查的第一首诗就是大地的赞美诗,那首诗总结起来所以孔子在说到文学心兴是第一,兴就是赞美。
“观”就是你的写作要为你这个部落的人提供你对世界的看法,就是我刚才说的你的声音要能够吸引他们,使他们不再害怕不可知的力量,观点。
“群”就是你的观点能够团结你这个部落的人,如果你只是个人写作,你不能团结人,所以大家就不听你的声音。为什么今天当代文学越来越衰落?你不能群了,你的写作只是变成你个人的自我表演,你可以表演我也可以表演,我凭什么看你的表演,就是不群了。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就是秩序,尊重。文革后,这个已经完全乱了。
“怨”是一种批判,今天是一个怨的时代。因为赞美的时代结束,另外一个世界,过去对于我们来讲永远是一个不可企及的黄金时代,那就是黄金时代。今天只剩下一个怨,还有一个多识,文学最后变成一种修辞的知识,太可怕了。
今天有很多诗歌变成一种语言的装修活动,不群,不能团结,不能再共享,你的作品出来最后变成一种商品的生产,你不再和读者发生任何关系,你写出来然后你和新闻界发生关系,你和批评家发生关系。今天这个已经是很严重了,有很多人你是知名作家,没有人知道你写的是什么,我也是这样。写作本来有指鹿为马的功能,现在是鹿都不要了直接生产那匹货币之马。
写作也受到这种影响,它仅仅在制造一些象征,至于是否能够共享、是否能够使读者重新意识到生命美好,全不在乎。我们还是应该活下去的,那么如果读者在你的作品里面完全看不到这种东西,他就不会读你的作品。
今天文学的态度我觉得可怕,你不读我们就自己玩自己的,变成一些小圈子。那么我最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西方文明玩剩的过程,你去玩什么形式主义,玩修辞,玩结构,我不和读者发生关系,我就是自我的一个表现,这也是西方玩剩的。前几天我还在巴黎参加一个诗歌市场,巴黎每年有两天的诗歌市场,我们刚进去的时候,我们真是非常惊讶的,那个广场在教堂前面,广场上中间是伏尔泰的雕像。下面摆着一百多个摊位,法国的诗人告诉我,在法国有三百多家诗歌出版社,我觉得太夸张了,中国连一家诗歌出版社都没有。虽然有诗歌已经和市场这个词联系起来,但是它市场并没有成为西方写作的全部。梦想着自己成为不朽的能够进入卢浮宫的作家还是有一大批,很多,就是那个诗歌市场也在卖这些诗人的诗集,还是在产生那种真正的要招魂的诗。
作者简介弗朗茨?卡夫卡(—),奥地利作家。出生于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布拉格的一个商人家庭,犹太血统。始终接受德意志文化教育,用德语写作。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年就职于一家工伤事故保险公司,直至年病退。年罹患肺结核,最终死于喉结核。一生坚持业余写作。生前出版过四部短篇小说集,年问世的短篇小说《判决》是他的成名作,除《判决》外,《变形记》《司炉》《在流放地》《乡村医生》以及《饥饿艺术家》均为他本人认可的短篇代表作。还留下三部长篇小说遗稿,即《失踪者》《诉讼》和《城堡》。此外还写有大量书信、日记和随笔,亦具有很高的文学和思想价值。一生中有过多次恋爱,并曾数次与人订婚,但终身未娶。
晚年曾有毁稿之念。死后多亏其挚友马克斯?勃罗德一一整理并出版了他的遗稿乃至全集。20世纪40年代起受到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兼作家萨特、加缪等的高度赞赏,此后引起世界范围的巨大反响,有“现代文学之父”的美誉。
内容简介主人公K应聘来城堡当土地测量员,经过长途跋涉,穿过许多雪路后,他终于在半夜抵达城堡管辖下的一个穷村落。在村落的招待所,筋疲力尽的K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他们都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平民。其中有招待所的老板、老板娘、女招待,还有一些闲杂人员。城堡虽近在咫尺,但他费尽周折,为此不惜勾引城堡官员克拉姆的情妇,却怎么也进不去。小说至此戛然而止,为读者留下许多悬念……
赞赏
长按向我转账
受苹果公司新规定影响,iOS版的赞赏功能被关闭,可通过转账支持。
北京哪个白癜风医院比较好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路线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dihd.com/zcmbzl/8337.html
- 上一篇文章: 历年银河奖获奖作品回顾第24届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