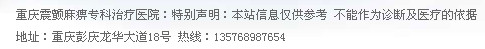小众专稿东君一个与古为徒的人
李晓君说东君:一个“与古为徒”的人
我时常会想起那个时刻:在东八里庄鲁院三楼一间宿舍里,与东君、玄武就着一些咸虾子,喝啤酒。虾子,还有鱼干之类,来自于被东君习惯称之为“东瓯”的温州。四月,北京的泡桐花和槐花开得沉静而亮丽,时光机,在缓缓地旋转,一段仿佛从生命中分叉出来的光阴,将我们聚合在一起。那样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是诗意和温情的。咸虾子,干鱼,让我想起孔乙己先生的茴香豆和黄酒。而这些东西,都来自于鲁迅的故乡,也来自于东君的故乡——那个临海的南方省份。因而对东君习惯于称之为“东瓯”的温州——这个至今未曾踏足的地方,感到好奇。在党报和其它媒体中,那是个被商业头脑充斥的城市,东方的犹太人足迹遍布全球。但东君给人的印象,仿佛与此毫不关联,他文质彬彬,举手投足之间,有一种夫子气的迟缓和儒雅,像是一个从古代走来的人。
难以置信,这曾是一个习武成癖的人——他本来就是一个拳师的儿子,因而文质彬彬、甚或有些羸弱的他,居然臂力惊人,为此,他曾与同学中一位粗壮的汉子比划过。这个习武者,同时也是一个粤语歌曲爱好者,一个喜欢出游、说笑、搞怪的人,一个女孩的父亲,一个恋书成癖者——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喜好书并藏书无甚奇怪,但东君那来自于许多野史、民间文献和其他晦涩难懂图籍的知识,多少有些与众不同。他将他一部分作品冠之以“东瓯小史”,里面许多似曾相识而又陌生的形象——拳师、弹琴者、清客、乡绅、养鹤人、隐居者、种花人,都不像是活在当下喧嚣社会的人物。在他那首《与古为徒》的诗中,他写道:“我的左邻是老子与庄子/我的右舍是孔子和孟子/荷尔德林跟海德格尔是近邻关系/正如梭罗和身居闹市的我/……/我忘记诗经,然后开始写作/我忘记所罗门箴言,然后开始写作/我忘记陶渊明、杜甫、苏东坡,然后开始写作/我忘记但丁、叶芝、布罗斯基,然后开始写作//忘我,然后发现另一个我……”这简直就是他的写作自白——从中我们可以管窥他的写作谱系,知识来源。我以为,将中国的古典主义与西方的现代主义结合得如此之好,在当代作家中,他是最出色者之一。
东君赖以成名的作品,带有鲜明的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痕迹,他的这些早期之作,不难看出博尔赫斯、卡夫卡、加缪等人的印记。因而,如同大多数年轻作家一样,沿着现代主义小说道路狂奔,直捣它的中心——这是东君进入小说的方式。然而,让人吃惊的是,东君近几年的小说,却散发出一股浓烈的“复古”主义气息,一种中国式的典雅和醇厚。他的小说没有庙堂之气,故事的发生地多在民间,那些多少带点侠气、士气、隐逸风度的人,身上没有一丝“俗吏”之气。我对那些故事好奇并感兴趣。由此,便回望这个曾经负笈同窗的人——应该承认,这是个有趣的人,一个浪漫的人。
东君的浪漫不是可以一眼望穿的。恰恰相反,大多数的情况下,他可能给人一种讷于言辞、学究气和慢热的形象。其实东君的浪漫之心是无人可比的。在他恶作剧和突发奇想的举止里,没有一丝轻薄和浮浪之气,而是一种雅趣,一种天真和单纯。由此,你会愈益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我们陌生已久的——士气。我有时寻思,他的这种气息,究竟从何而来?而他刻意不刻意追求的这种东西,是为了什么?
倘若没有东君,我们几个——王十月、李浩、马笑泉等人,对书画的兴趣,不会变为一种实际的行为艺术,不会堂而皇之地结社切磋。东君是倡议者,也是热情的组织者。需要提及的是,此后,回到温州的东君,还曾策展过一次并非商业性质的中国当代作家书画摄影展,分别在沪上和东瓯与寥寥的观众见面。东君致力于发掘久已丧失的“贵族气”、“文人气”,是一个真正愿意“与古为徒”的人,这份谦虚里,饱含着巨大的敬畏和自信在里面。他沉静、绵密地去做一件事,就是反僵化和呆板的东西,尽管进入古典,往往会给人一种僵化和呆板的错觉。
他是一个真正读懂中国传统的人——他拈取的是传统里最精华和动人的部分,是在文学上“中体西用”的虔诚的实践者。东君曾经戏称自己是个“东西南北中”的人,如同在《与古为徒》诗中展示的,他着意在东西方、传统现代之间,找到一种文学表达上的平衡,找到一个发力点,这是东君近些年来深入传统而新意别出的原因所在。
东君好书尺牍,尤善小楷。纯粹做个小说家,对他来说,并不满足。他的诗歌、散文,同样出色,而小楷不走“二王”、赵孟頫、文征明等路子,善于从北碑中取法,书风有一种野逸、宽博、浪漫之气。米兰·昆德拉说:“科学的发展很快将人类推入专业领域的条条隧道之中。人们掌握的知识越深,就越变得盲目,变得既无法看清世界的整体,又无法看清自身……”而东君却努力打通文、史、哲、宗教与书法,从而获得一种文化上的整体观,是殊为可贵的。
李浩有句名言:“打不死的南方人。”这句戏谑的话,用在东君身上合适。他立足于南方,在浙东南的海边,在他所谓的“东瓯”,一头扎进古典中国的深处,田野采风,精耕细作,采用第一手的民间文书和地方资料,力图在把握孔孟佛老基础上,中国化地表现温州这块带有历史感和文化感的土地。年,从日本归国的傅衣凌,在福建永安离城十多里的一间乡间老屋里,无意中发现一箱民间契约文书,在研读的基础上写出了史学界颇为重视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而东君对民间文献的重视,以及他多年来对西方文学的消化吸收并形成的一套系统的文学观念,有助于他从一个宽的视野来理解文学、理解当下和书写中国故事。假以时日,他的带有乡风民俗气质的小说,他以传统为背景切入当代人内心深处的表达,会显得更加别致和醒目。
东君爱唱粤语歌曲《小李飞刀》,这个崇尚侠气的玉面小生,仿佛一个手持利刃的刺客,双手舞弄着花样百出而招招致命的利器,向我们走来——这不是一个蒙面皂衣的刺客,而是一个穿牛仔裤、花T恤的刺客,这个带着眼镜、嘴唇微紫的后生,手中的利器不过是一册书而已。可能是《圣经》、《中庸》、《六祖坛经》,也可能是《某某年谱》《某某行状》之类,在他探囊取物、直取命穴的招式后面,有太多漫长的白日和岑寂的夜晚练就的真功夫——像南方夏天的日光一般锋利,也像南方冬日的海边一般湿寒……
东君说小说:小说是什么?
小说不仅仅只有“说”。小说如果只是“说”——说故事,那么小说家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说书人。听父辈们说,我们镇上从前就有一种艺人专以说书为糊口职业(当然也有人以此为乐),他们端坐树下,穿长袍,面容安详,有古人气息。谈的呢?上至天宝遗事,下至街坊趣闻。这些故事,须是放在一种大众喜欢的话语场里头,偶尔打个闲岔,说段掌故,有噱头,有悬念,有散讲意味。很多人都知道,中国话本小说的传统来自于说唱文学,直至清末,遗风犹在。现在翻看那些小说,便可发现,彼时的小说家说着说着就会唱起来,吟几首诗,发一段感慨。而西方小说缘于古老的叙事长诗,也有说唱成份,但后来,唱的部分发展成抒情诗,说的部分演变为小说。说唱艺术作为亚文学的叙述形态,一直以来对小说的发展不无助益。从一种带有娱乐功能的公共写作转变为一种个体写作,最大的区别就是,“说”的方式不一样了。也就是说,那种诉诸“客官”的“说”变成了一种中医如何治疗白癜风补骨脂针剂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dihd.com/zcmbzz/7115.html
- 上一篇文章: 诗魂张曙光的诗
- 下一篇文章: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胜利80周年专题小故